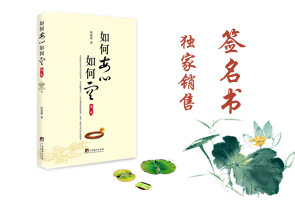关于“开悟”的五则公案
源自:《悟:禅宗的存在价值》 作者:铃木大拙
获得新观点在禅宗叫“悟”,无悟则无禅,因为禅的生活是从“悟”开始的。“悟”可以定义为与理性逻辑理解相对的直觉性洞察。
但我们先不必拘泥于定义如何,“悟”意味着在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中被隐没的、至今未被注意到的新世界的敞开呈现。请记住上面所说的这一点,并看一看下面的禅语录,我想,各位会明白“悟”究竟是什么。
初入丛林的一个僧人向赵州请教“心要”,赵州问:“吃粥了也未?”僧人答:“粥了也。”赵州应声说道:“洗钵盂去。”于是僧人突然大悟。
对此,云门评论道:赵州这番话中有什么特殊涵义吗?如果有,那是什么?如果没有,那么这个僧人又悟出了什么?但翠岩则反驳云门说:云门禅师理解得也不干净利落,所以这样评说,完全是画蛇添足,在宦官脸上添须。我以为,这个僧人没悟个什么,只是栽入地狱而已!
赵州的“洗钵盂去”,僧人的“悟”,云门的评论,翠岩的断语——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?是互相贬损,或只是大惊小怪?依我看来,它们都是指示着一条路。无论上述僧人向何处去,他的悟当然也绝不是徒劳。
德山是《金刚经》的权威,有一次偶尔听说禅宗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之说,便到龙潭那里请教。一天夜里,德山在门外打坐思索禅的奥秘,龙潭问:“何不入内?”“因为里边真暗。”龙潭便点烛给德山,德山刚接过,龙潭一口吹灭。当下德山心灵豁然大悟。
百丈陪其师马祖外出,偶然见野鸭子飞,马祖问:“是什么?”“野鸭子。”“甚处去也?”“飞过去也。”马祖突然扭住百丈的鼻头,百丈负痛失声,马祖说:“纵然如此仍道飞过去了么?不是一直在这里吗?”这一句话使百丈背上冷汗顿出,于是大悟。
百丈陪其师马祖外出,偶然见野鸭子飞,马祖问:“是什么?”“野鸭子。”“甚处去也?”“飞过去也。”马祖突然扭住百丈的鼻头,百丈负痛失声,马祖说:“纵然如此仍道飞过去了么?不是一直在这里吗?”这一句话使百丈背上冷汗顿出,于是大悟。
洗钵、吹烛、扭鼻,这之间有什么联系,我们要依照云门:“如果没有,那么他们为什么悟到了禅的真理?如果有,那么这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?而这悟又是什么?这是什么样的新观点?”
宋朝的禅师大慧手下有个叫道谦的和尚,多年习禅却未能开悟,他十分绝望。他常常被任命为使者派往远方城市,在路上要奔波半年,他想,这更会妨碍他研究禅理。他的朋友宗元对他很同情,说了如下劝慰的话:“我也和你一起去,虽然我仅有微力,但会尽力帮助你,即使一边赶路,也可以一边用功。”一夜,道谦哭诉道,愿请他帮忙解决一生的心事,宗元说:“途中可替的事我尽替你,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,你须自家支当。”道谦恳切地问其详,宗元说:“着衣、吃饭、屙屎、放尿、驮个死尸路上行。”道谦当下领悟,不觉手舞足蹈,于是,宗元便告别:“你此回方可通书,宜前进,吾先归矣。”道谦便一人继续前行。半年后,他完成使命回到寺里,正巧大慧偶然下山,路上碰见,大慧看着道谦的脸,说:“你这回别也。”
试问,友人宗元向道谦说了那番恳切的忠告后,道谦心头闪现出的是什么?
宋代著名的儒学家、诗人、政治家黄山谷初到晦堂处学禅,晦堂说:“只如仲尼道二三子‘以我为隐乎,吾无隐乎尔’者,太史居常,如何理论?”黄山谷正准备回答,晦堂制止说:“不是,不是。”于是黄山谷大惑不解,无言可对。此后,两人曾在山中散步,当时正好木樨盛开,香气四溢,晦堂说:“闻木樨花香么?”“闻。”“吾无隐乎尔。”黄山谷于是恍然大悟。
在上述各例中,我想已经大体可以说明悟是什么,如何获得悟了。但也许会问,“细读你的说明指示,仍有未尽明白处。假如‘悟’总是有某种内容的,那么难道不能清晰地加以记述吗?您举的事例和您的论说大多是心理意图性的,所以我们所明白的仅仅是风的方向,而那只小船最终究竟应该停泊在哪个港口呢?”
对于这个问题,禅者会这样回答:在内容上,悟也罢,禅也罢,凡是能被理性理解的可以证示、记述、提示的东西一概没有。因为禅与概念没有关系,悟是一种内在的知觉——不是对个别的对象的知觉而是对实在本身的知觉。悟的最后归宿是自身(self),除了回归到自身之外别无他处。所以赵州说“吃茶去”,南泉说“这茅镰子我使得正快”。自我正是这样运动的,如果要把握它,就必须在这“运动”中去把握。